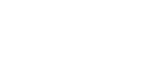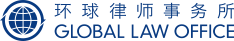2025年9月,某知名头部游戏公司法务部发布视频,展示其在“打击游戏泄密专项行动”中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某传播未公开游戏内容的泄密者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年来,部分群体通过私下偷跑的形式,早于游戏开发公司泄露游戏角色信息、活动内容的行为时有发生,这类以提前泄露游戏内容信息获取流量并牟利的群体被游戏社群统称为“内鬼”。提前剧透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游戏更新内容的悬念与吸引力,对游戏公司造成巨大影响。然而目前游戏公司所能采取的主要救济途径集中于民事赔偿与行为保全,对此,该公司法务部采取刑事控告手段并最终由公安机关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这一案例无疑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惩治带来了全新的启示。
从官方报道来看,此次受到打击的典型泄密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搬运”类和“解包”类,泄密对象则通常为游戏角色(系该类游戏的主要卖点)、场景、技能动画等。同时,有大量的游戏未公开内容以非美术资产的形式呈现,比如未来版本的卡池内容、运营活动、玩法机制调整等信息。以上信息尤其是卡池内容信息已成为游戏泄密的重灾区,影响极为恶劣。本文拟从信息被泄露的具体行为模式来具体探讨分析前述“泄密行为”的刑事控告路径,以期更有力、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经营权益。
一、侵犯商业秘密罪
(一)被泄露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性质
1. 商业秘密类型的认定
在游戏泄密的场合,首先需要判断被泄露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的典型形态分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以下简称《规定》)将经营信息定义为“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应当认为被泄露的游戏信息属于经营信息的范畴。
实践中,已有多份判决将游戏未公开内容认定为经营信息。例如法院在“上海米某游影铁科技有限公司与陈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将未公开角色设计认定为经营信息,并提出了经营信息的如下判断规则:(1)权利人在经营活动中通过长期不懈努力的创新、创造或积累所获得;(2)对权利人开展经营往往具有核心竞争价值。“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诉陈某侵害经营秘密纠纷案”也采用了相似的判断规则,认为经营信息的法律特征为投入劳动和创造营业收入、增强竞争优势。但是,上述对于“经营信息”的论证已经涉及“价值性”等要件的范畴。实际上,《规定》对于经营信息的要求并不严格,只要是与经营活动有关的信息即可。游戏角色、场景等信息确实与游戏的运营有关,属于经营信息并无疑问。
2. 经营信息的价值性:“二游”模式的特殊性
经营信息型商业秘密要求信息内容符合“秘密性”“保密性”“价值性”的要件要求。在新游戏或新版本公布前,相关信息尚未公布于众,游戏公司也通常会与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秘密性”与“保密性”要件通常不是构罪障碍,但是“价值性”要件可能存在疑问。技术信息的“价值”确认无虞,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亦几乎将之作为默认的要件。然而相对于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究竟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价值增长,却是一个难以量化的因素,进而,其“价值性”也受到了不少挑战。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86号)作出了规定:“本规定所称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在司法实践中,也采用“竞争优势”作为价值性的判断标准。在“上海米某游影铁科技有限公司与陈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涉案游戏版本更新前后,其排名、热度、收入预估、下载量预估趋势等数据均呈现较大幅度提升,据此足以认定涉案游戏前述运营模式也能为权利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对于游戏公司而言,游戏版本更新前后,其排名、热度等数据的大幅度提升,足可见得版本信息的价值和对游戏热度、经营现状的直接影响。玩家愿意更新版本或是新玩家加入游戏,不仅源于游戏提供了高质量的游戏体验服务,更在于新版本所带来的全新体验,有期限的角色、活动更是会吸引大量玩家群体涌入。因此,作为经营信息,版本更新内容会直接影响到游戏在更新周期内的直接表现,而游戏更新后的火热程度,又会直接影响行业对该款游戏甚至背后开发公司的评价与认可度,竞争优势凸显无疑。被泄露的版本内容的价值性由此确认。
(二)客观行为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要件
1.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
从客观行为来分析,“搬运”类泄密主要涉及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特定商业秘密信息,主要指将未公开内容拍照或录屏外传的行为,对此类行为的界定往往并非难题。
一方面,侵犯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与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客观行为的表述规范层面高度一致,因此,在刑事控告上,只要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符合侵权规范,则其行为往往也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也规定,采取非法复制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窃”,以拟制的方式解决了行为认定的困境。因此,行为人违反约定进行拍照、录制、截屏的行为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此外,不难发现目前司法解释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行为阐释相对宽泛,这也为以刑事手段打击“内鬼”行径提供了必要帮助。
2. 违反保密义务
除上述行为以外,游戏公司会在特定测试期间向其所邀请的媒体单位或者测试者提供限定的信息,部分行为人借此接触并传播信息内容。例如,以“解包”的方式,通过反向编译破解游戏安装包内的数据文件,从而获得获取未公开游戏内容的源代码并公开传播。一定程度上,游戏公司允许特定人群在限定范围内了解版本更新内容,并对此加诸严格的保密义务进行保护。对此,行为人接触信息的过程或许符合法律规范,但其违背保密义务进行不当宣传的行为仍应当追究责任。
《刑法》第219条第3款规定的是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对于该行为模式,《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曾经规定为“违反保密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将“违反保密约定”改为“违反保密义务”,为保持与前置法的协调,刑法修正案(十一)作了对应的修改,是对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客观要求。
针对“解包”等方式,游戏公司为了确保更新信息不被泄露,内部测试时期,均会对以多种形式未公开内容设置严密的保护义务,即便行为人或许信息时不存在违法性,在未经公司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不当泄露亦会形成对保密义务的违背,进而触犯本罪。
(三)实践困境
从行为规范的角度而言,相较于通过民事手段维权,以刑事控告的方式认定行为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对类似行为必然具有更强的震慑力,然而目前的司法实践下几乎没有以刑事犯罪认定的判例存在,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少实践难点亟待克服。
1. 经营信息的保护
在当下,因经营信息而被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比例相对于技术信息而言,仍仅有一小部分,这不单是源于对经营信息保护的理念滞后,更源自于一般经营信息的“通病”,即在商业价值、保护措施和知悉程度上均存在一定瑕疵。
然而相较于一般作为经营信息认定的客户名单、生产计划、招投标材料等材料,游戏公司未公开版本内容实质上已经在认定难度上有所下降。从信息保护的程度而言,其他经营信息或许还存在口耳相传、不加限制等问题,进而影响“对该秘密信息提供了充足保护”的认定,游戏公司实质上较为重视版本更新的内容和信息释放的节奏,这一点从每期“版本前瞻”的关注和讨论热度中就可以体现。价值性的论证已有前文论述,相较于一般经营信息体现为潜在商业价值的特质,游戏公司的版本更新内容往往与下一版本的消费热情、每日活跃人数等重要经营指标直接挂钩,价值认定亦可解决。而对于“非公知性”则可以通过层层设置的保密义务来体现。
据此,可以认为实际上较之其他信息内容,游戏版本更新内容在商业秘密的性质认定上更具优势。
2.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民刑衔接
困扰刑事救济途径的另一重因素则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之间的边界模糊,衔接方式亦未有清晰规定。
比较商业秘密保护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与刑法规制,两者在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客观行为表述上基本一致,客观行为的类型难以成为区分标准。因此,从法律条文表述来看,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方式相同,区别主要在于行为的危害后果和主观心态。因此实务观点倾向于认为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只有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给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数额,可以作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的较为具象的判断标准。
此外,虽然规制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并不复杂,但是二者承担功能存在本质差异。侵犯商业秘密罪位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通常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体除权利人对商业秘密享有的合法权益外,还包括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相较于财产权益的保护而言,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法益更为多元。《中国检察官》2025年第5期所刊登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民保护边界的厘清》一文中也提及,在判断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时,还需要进行实质违法性判断,即考虑涉案行为是否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了实质性的破坏。因此,行为法益侵害的程度,可以作为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抽象的判断标准。
也只有充分辨析清楚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与侵犯商业秘密罪之间的界限,才能更准确的分析和讨论对“游戏内鬼”行为的规制,是否足以上升至刑事手段。
二、破坏生产经营罪
除了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等相对常见的法律救济途径以外,以刑事手段进行规制还可以向其他罪名进行延伸与探讨,尤其在以网络经营逐渐成为现代生活主流模式的当下,这样的讨论更显意义,其中较为典型的即是破坏生产经营罪。
(一)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构成本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罪状规定采用了例举加兜底规定的形式,除毁坏机器设备和残害耕畜是两种原本较为常见的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方式外,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也构成本罪。而“其他方式”的范围和边界即为“内鬼”行为是否契合构成要件的核心。
而如何理解“其他方法”在理论界尚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严格遵循同类解释规则,仅应当包含对具象生产设施的破坏。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对生产经营的破坏行为,就是“其他方法”。[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其他方法”的解释需要遵循同类解释规则,但“同一类型”应当归纳为“破坏生产经营核心要素”的行为。[2]
对于以上三种对“其他方法”的理解,采用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第一种观点过于教条,难以规制网络空间中的破坏生产经营行为,不应采用。第二种观点虽然可以弥补上述缺陷,但已经完全抛弃了同类解释的约束,相当于排除了行为要件的要求,极易陷入唯结果论的窠臼,进而为本罪的口袋化大开方便之门,[3]因此也应当摒弃。第三种观点既尊重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解释的要求,又能涵盖网络时代的破坏生产经营行为,更为合理。《刑法》显然无意让渡对网络空间破坏生产经营行为的规范,使其成为“无法空间”。因此仅观察条文所列举的类型可能导致对条文理解的偏差,必须结合目的解释探寻该要素的本质特征。
虽然本罪位于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下,但亦不能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简单理解为保护特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所有权,脱离了生产经营活动,上述特定所有权相对于普通财物并无特殊保护的必要,因此本罪的保护对象应当理解为生产经营活动,条文中的“其他方法”应当理解为“破坏生产经营核心要素”的行为。
实践中,将本罪的“其他方法”拓展至“破坏生产经营核心要素”的做法已较为常见。例如,堵塞施工道路、阻止运输从而影响施工进度的行为历来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4]堵塞道路不同于毁坏道路,没有对生产设施造成物理破坏。同时,在电商领域,诸多新型以非有形力破坏生产经营行为被认定为本罪。无独有偶,多地法院将恶意好评或差评炒信的行为认定为“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5]将篡改店铺发货时间、商品价格的行为认定为“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6]等,均是在网络经营时代对“其他方法”的合理诠释。在上述案例中,行为人均没有对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施加有形力,但是其行为对生产经营的核心要素造成了破坏:物流链、商业信誉均直接关系到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亦印证了上述“以生产经营核心要素”为判断标准的合理性。
(二)游戏行业的生产经营核心要素
具体到游戏泄密行为,因游戏角色、剧情、卡池内容等信息公开时间对玩家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破坏宣发节奏的行为可以被认定破坏关键生产要素,构成“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游戏角色、剧情、卡池内容等信息不是单纯的美术或文本,而是直接绑定玩家情绪进而影响游戏收入的重要信息。提前泄露此类信息的重大破坏性在于破坏了因新鲜感、好奇带来的消费感。在游戏行业,游戏首日流水对于整个周期流水具有重要意义,“首日即峰值”的现象广泛存在。
例如2025年4月初,某知名头部游戏公司推出2周年庆典更新版本,更新首日游戏流水快速飙升至1周年庆以来的最高值,登顶中国、日本、韩国等多市场iOS手游畅销榜,但在月底又回落至20名之外;[7]6月17日,某游戏正式推出5.7版本,更新次日即登顶iOS游戏畅销榜,但同样在月底回落至30名左右。[8]由此说明,游戏更新带来的消费热情是玩家付费的重要动机。若游戏角色、剧情提前泄露,则会导致二创、吐槽、返工声量瞬间爆发,把原本集中在上线当天的付费想法提前稀释甚至直接掐灭,更枉论内鬼信息并不完全准确,从而造成负面宣传的行为后果,与现行案例中的“反向刷单”高度一致。
卡池内容提前曝光的影响更为直接,卡池顺序、抽到稀有物品的概率信息直接关系到玩家的消费行为,例如未来卡池将推出重要人物的信息若被提前透露,玩家很可能集体停止在当前卡池的消费,提前囤积虚拟货币,如此游戏当月的收入就有可能暴跌。因此,固定的宣发节奏,即游戏公司根据计划在固定的时间发布固定的信息对于游戏经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纳入“生产经营核心要素”的范畴;破坏游戏的宣发节奏透露重要信息直接影响到游戏收益,属于“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三)主观目的
在主观方面,构成本罪需具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对于“其他个人目的”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是“个人目的”,指行为人的目的与法益所有者的利益是相悖的,如果行为人的利益和法益所有者的利益是共同的,则不构成“其他个人目的”。例如在“刘俊破坏生产经营案”中,行为人出于扩大销售业绩以助个人升职的动机,违反公司限价规定,擅自低于进价销售电脑产品,法院认为行为人不具备“其他个人目的”。[9]该案中,行为人的目的获得晋升机会,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条件是扩大公司业务,因此行为人的个人目的和公司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不能属于“个人目的”。
第二是非正当目的,若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是正当目的,也不构成本罪。通过阻碍生产经营维护合法权益是典型的正当目的,法院通常认为此类情绪不符合本罪的主观要素。[10]在游戏泄密中,行为人泄密的原因通常是出于炫耀、获取流量或竞争公司收买,以上动机均与游戏开发者的利益明显相悖,且不具有正当性,属于本罪所要求的“其他个人目的”。
据此,虽然现行判例并无体现,但理论上游戏“内鬼”泄密的行为从主客观等方面均契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存在适用该罪对类似不法行为进行规范的可能性。
游戏厂商常年对“内鬼”行径深恶痛绝,却很难对其采取有效遏制,因此,如果能在刑事救济方式下形成可实践、可复制的惩处路径,将会有力震慑泄密行为的猖獗表现。“钟馗捉鬼”,必有一法可用!
注释:
[1] 参见高艳东:《破坏生产经营罪包括妨害业务行为——批量恶意注册账号的处理》,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年第2期。
[2] 参见黄弘毅、程骋:《网络时代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其他方法”:基于客观解释的立场与实质解释的限度》,载《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徐久生、徐隽颖:《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3] 参见徐久生、徐隽颖:《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4] 参见武某1、冯某等破坏生产经营案,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法院(2024)晋1129刑初125号刑事一审判决书;程某、仲某破坏生产经营案,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8刑终144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5] 参见董某、谢某破坏生产经营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刑终33号二审刑事判决书;钟某破坏生产经营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刑终602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6] 参见倪某破坏生产经营案,河北省威县人民法院(2021)冀0533刑初77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7] 参见手游那点事:《手游出海要挤不下了:点点新作激增209%,月流水已破1900万美元》,载手游那点事5月15日,http://www.nadianshi.com/2025/05/388473。
[8] 参见游戏那点事:《低调却偷偷爆发:米哈游收入涨32%,库洛飙升55%,雷霆创1年新高》,载今日头条2025年7月9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25082668682330624/。
[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至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4(侵犯财产罪)》,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96-500页。
[10] 参见孙某破坏生产经营案,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吉0323刑初82号一审刑事判决书。